一、关于原著小说
《白鹿原》是作家陈忠实的呕心之作,中国当代乡土小说的代表作。有人说它是一部浓缩的“民族史”。主要描写了 20 世纪初到 20 世纪中叶,以关中大地白鹿原白鹿村,白和鹿两个家族两代人的生命史与恩怨交缠为大主线的乡村与社会的变迁史。(小说主要展现了两代人,电视剧展现了三代人)

那是一个经历了几千年未有的大变革的、剧烈动荡、激浊扬清又泥沙俱下、渴望进步又翻云覆雨的年代。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由原初还算可控可把握的稳定和秩序,走向无序和荒莽、礼崩乐坏,又试图挣扎着向往新生的年代。这个古老国家承载的一切厚朴、沉郁、悲怆、悖谬的本色,在小说里展现的淋漓尽致。
新生最终到来了,却不是按照任何人的简单朴素的希望的方式到来,它已经因为人心和人性的荒芜凋敝而满面皱纹,少有温情底色可言。每个人都被时代不可抵触与挽救地绑架,无论精神还是肉体。因此作为白鹿原白鹿村的两大精神图腾的象征,祠堂和朱先生,最终都无可避免地凋落远去。祠堂的凋落不可惋惜,但是朱先生的凋落,却是白鹿原最可悲悯的悲剧。
事实上,原书中的主要人物,除了朱先生、白灵、黑娃和田小娥,其他人身上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甚至可以说严重的人性以及人格缺失。在以亲情和血缘为纽带串连的乡村社会关系中,这几个人物跳脱了出来,最起码,是在努力尝试以我心谱生活。而其他人呢?则如被线控的傀儡木偶,被无量多的心外之物所控。
而这里面最突出的代表,就是鹿子霖。他是典型的被名利、欲望所控的人物代表。白嘉轩,这个全书着墨最多,最被着力刻画的人物,则是被传统、礼教、以及对好名声的追求与标榜,所控。坚持原则、坚守心中的道义,是优秀的品质,在乱世中能葆有这些品质,尤其可贵。但是,固守宗法,对田小娥的困境毫无怜悯,毫无底线地为“尊者”讳,把自己物化为一个机器怪物般顽固无情的宗法执行者,却是一桩憾事,也说明,这个总希望聆听圣人教诲的人,并不能理解圣人的智慧,从而一手造成了自己及自己家族所蒙受的最大悲剧。
同时,白嘉轩这个人物身上还有更深一层的复杂性。他身上综合了传统美德——对仁义的追求(虽然他对田小娥完全谈不上仁义,也就是说,他的仁义是有区别对待的。后期白孝文的妻子在家中活活饿死,也令人怀疑他的仁义到底是做给人看的,还是心中真有仁义),勤劳朴实,身为族长的正直、无私,同时还夹杂着小农的狡猾、自私与短视。做戏和鹿子霖换地,以及自己首先在白鹿原开了种植罂粟的先例,都是这个人物复杂性的表现。
然而最后,陈忠实还是手下留情的。白嘉轩最终与黑娃达成了和解(但是对田小娥,他有过愧疚吗),但也无能为力地看着自己的儿子,成为新时代的兴风作浪者。革命队伍里混进了投机分子,而投机分子最终会把一锅好汤搅得变味。这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人性的悲剧。
原著小说在前半部分,并没有写得多深刻,后半部分,大概是随着史料增多,以及最大化的感同身受,而写出了更深层的东西。在整体上,完成性和人物塑造的有力性,不如后来的电视剧版剧作。电视剧版剧作,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改编,即抓住了原作的精髓,充分展现和传达了原作的精神,同时,也更为细腻和丰富,使人物更为立体、鲜活、可信。而且,在价值和精神层面的传达上,做出了升华的效果。
这种效应大概可以说明,看待一段历史,一个人物,需要站到一定的距离——空间和时间之外,才能看得更清、更全面,也把握的更准。
二、关于电视剧剧作的改编
要改编一个作品,首先要做到的是理解这个作品。要书写一个人物,首先要做到的是理解这个人物。《白鹿原》电视剧版的改编者,编剧申捷,显然做到了这一点,而且做得青出于蓝,锦上添花。
由于小说的前半部分戏剧性不强,人物特色也不算凸显,因此编剧在前半部分给予了最大限度地整合改编,完全突破了原作的一些设定以及细节。首先是人物基调的确立和人物关系的梳理。我认为编剧做的非常成功。编剧首先大刀阔斧地砍掉了一些与主线无关的人物,以及内容情节。比如,原作中仙草的身世是白家一个药铺伙计(后来升级成药铺老板)的女儿,并非山中逃难的贫户之女。白嘉轩还有另外一个在城里生活的二姐等,这些无益于集中展现白鹿原农耕生活圈的因素被果断剥离了,却增加了白嘉轩和鹿子霖两家父辈的戏份,以让观众直观看到主角们所面临的家庭氛围或者压力,同时增强代际人物对比,说明编剧一开始就有一个全盘的、清晰的改编方向。
编剧给仙草重新安排了身世,同时,清晰化了鹿子霖和白嘉轩的人设:一个狡猾、一个朴直,性格对比强烈。原作中两人并不争抢族长之位,剧作中为了加强可看性,当然要安排他们争一辈子。原剧中娶仙草并没有费多大力气,剧作中,用一集的体量终于让白嘉轩娶到了如意妻子,同时,最起码四个人物立得很住:白嘉轩、鹿子霖,仙草和朱先生。
原作中朱先生退清兵,也没有那么强的戏剧化,但是剧作中,却写得精彩无比。虽然剧作中的朱先生已经变成了中国传统社会所能培育的完美人格和人物的代表,但并不让人觉得虚假。有智谋、勇力、仁爱、侠义,并有着浓浓的人情味,以及清醒之心,并不失幽默感。大家喜爱、敬重朱先生,把他奉为圣,奉为神,也是理所应当的。
剧作的改编技巧纯熟,驾驭冲突和节奏游刃有余,人物和对白精彩,常有点睛之语。后期剧本的改编更多地遵循了原著。因为原著中原有的内容冲突和戏剧性已经很完备。尤其有大段的台词都是照搬原著,比如白灵被清党运动迫害致死前,对那个制造令亲者痛、仇者快惨剧的人的痛斥。这种痛斥太有力,也是精华所在,当然可以直接搬用。
虽然后半部,有很多内容和情节甚至对白都直接采纳了原著,但对白灵这个人物的塑造,编剧确也着实下了一番功夫,重新添加了不少的情节量。虽然白灵的经历中有一段仿佛令整个电视剧画风陡转,有向谍战局偏移的嫌疑,但还好,编剧及时收住了心中的洪荒之力。编剧的野心很大,想要比较完整地还原那一个历史时期,各种人物的命运沉浮,和时代特色,或者说,主基调(但也可能,之所以会在这个人物身上挥洒几乎有些把持不住的笔墨用量,也是为了加强最后人物命运带给人的冲突感)。
总之,对比《白鹿原》的原著小说,和改编后的电视剧剧作,可以让人很清晰地学到一些电视剧改编的重要原则和技巧。人物特色清晰化,冲突极致化,节奏明快化,适时加入幽默元素调剂作品气氛,甚至专门安排一些负责搞笑的人物,来凸显一些情节的荒诞,以及提醒观众,矫正立场。
但是另一方面,剧作也不可避免地简化了原作。同时为了让观众不至于对剧中的主要人物产生太大的反感,而对一些相关人物的命运进行了柔化处理。比如,白孝文的妻子在小说中被饿死了,但在剧作中,并没有。不然的话,可能对观众来说,这样的安排太残酷。
电视剧中这种的柔化处理还有不少。比如结尾。小说结尾鹿子霖发疯致死,电视剧却安排他和白嘉轩,一起到学校找小天明,两人悲欣交集,推着酷似少年白灵的小天明荡秋千,给观众一个期待中的圆满和美好结局:所有人际间的干戈纷争都可以止息,所有时代加诸在人身上的苦难颠沛也终有退潮,未来,还是有希望的。
三、关于书中和剧中女性角色的分析
全剧中最引发人关注和同情的角色,莫过于苦命的田小娥。
田小娥,既是一个欲望符号,同时也是一个不甘摆布,勇敢追求自身幸福和人间温情,却最终敌不过命运乖离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
从始至终,这个人物都是善良的,心怀希望的,没有做过什么出于本心的“恶”,但是,她却承受了整个农耕文明所能加诸于一个女人身上的最大恶意与敌视、排拒。
另一个让人同情的角色,是完美符合传统社会对女性的所有美德要求的冷秋月。这个人物就是送人头般的存在,她明明有选择,转个思路离开鹿家就能获得更美好的生活,却什么都没有做,眼睁睁任自己被折磨变疯,最后悲惨死去(这莫不是个双鱼座?)。这个人物身上NPC属性太过严重和明显,因此很难引起人更多的感受和关注。
可以说,全书中,除了白灵这个被特意塑造的新时代女性角色,以及田小娥这个异类,其他所有的女性无不是工具化的存在,没什么主体性,也没有个人价值。女人存在的最大价值就是操持家务,传宗接代而已。而女性们也都坦然接受这样的角色安排,并自觉自动地规划下一代女性,也变成和自己一样的角色。比如,剧中,白赵氏处心积虑地要给孙女白灵裹小脚。
说白了,传统的中国社会,就是这么一个对女性吃人不吐骨头的残酷社会。就连传统社会的完美人格化代表,朱先生,娶朱白氏,也是看中了她是最合适的相夫教子的人选。电视剧中并没有交代朱先生如何择妻,但是小说中却说得很清楚。女人们像是货物般等待挑选。(当然,如果公平来说,男性有时也是被这样物化挑选的对象,全看你所处的社会阶层和选择余地)
无论如何,剧作中《白鹿原》的希望落点,落在了新时代女性的代表白灵的小女儿——天明身上。这既是编剧的美好希望,也是现实中事物和社会的发展方向:我们今天,最起码已经跳出了一些窠臼,让更多的生命,得以按自己想要的,和应该拥有的方式,呈现自己。
总之,《白鹿原》已经看完了。希望它以后的生生世世,多点清爽明朗,少点乖离、沉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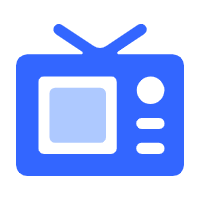 电视剧 第44章 白鹿原8.8
电视剧 第44章 白鹿原8.8


